翻译丨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政治(1)
时间: 2021-11-10 09:40:27 | 作者:Deutschesreich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0次
- ^除了法国大革命的短暂时期,驱使19世纪公共博物馆发展的通常是统计学家或者政府战略而不是对民主原则的信奉,因为这些原则自身都是不合格的。但这并没有阻挡回顾解释公共博物馆的发展和政治民主的发展,因为这些解释是本质上相关的现象。也许其中最激情澎湃的当属T. R. Adams在1939年做出的解释。对Adams来说,博物馆的典范和政治民主的典范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就像他说的:“一个中等城市里繁荣的博物馆可以当做全面民主的标志。”(Adams, 1939: 16)。
- ^于此类评价,参见Kasson (1978)。
- ^关于这种类型最有影响力的解释,参见Wittlin (1949).
- ^然而,爱德华兹的立场非常复杂,他反对要求图书馆的用户透露他们的职业,部分原因是这种要求的形式可能会阻止一些人加入图书馆。
- ^这一结论是基于Hudson (1975)的参观者研究的书目和Erp and Loomis (1973)关于博物馆行为举止的文章的参考文献。
- 2023-11-29 00:59:17有什么比较好玩的历史推理
- 2023-11-27 15:01:01历史流传下来有没有可能被人篡改 
- 2023-11-27 13:00:19年羹尧在历史上是个什么样的人
- 2023-11-27 12:01:38屈原为什么么能成为世界文化名人,中国历史中比屈原成就高的有很多,屈原怎么就可以是世界四大名人呢
- 2023-11-27 01:00:47如何评价历史上岳飞镇压钟相和杨幺起义军的举动
- 2023-11-26 22:01:29中国历史上的北狄和南蛮,谁更强
- 2023-11-26 21:00:18三跨文博or学科教学(历史)or中国史
- 2023-11-26 10:01:10中国人应该怎样评价历史上的李香兰
- 2023-11-26 03:59:53司马迁为什么被称为中国历史学的始祖
- 2023-11-26 01:59:57你对哪个历史人物最同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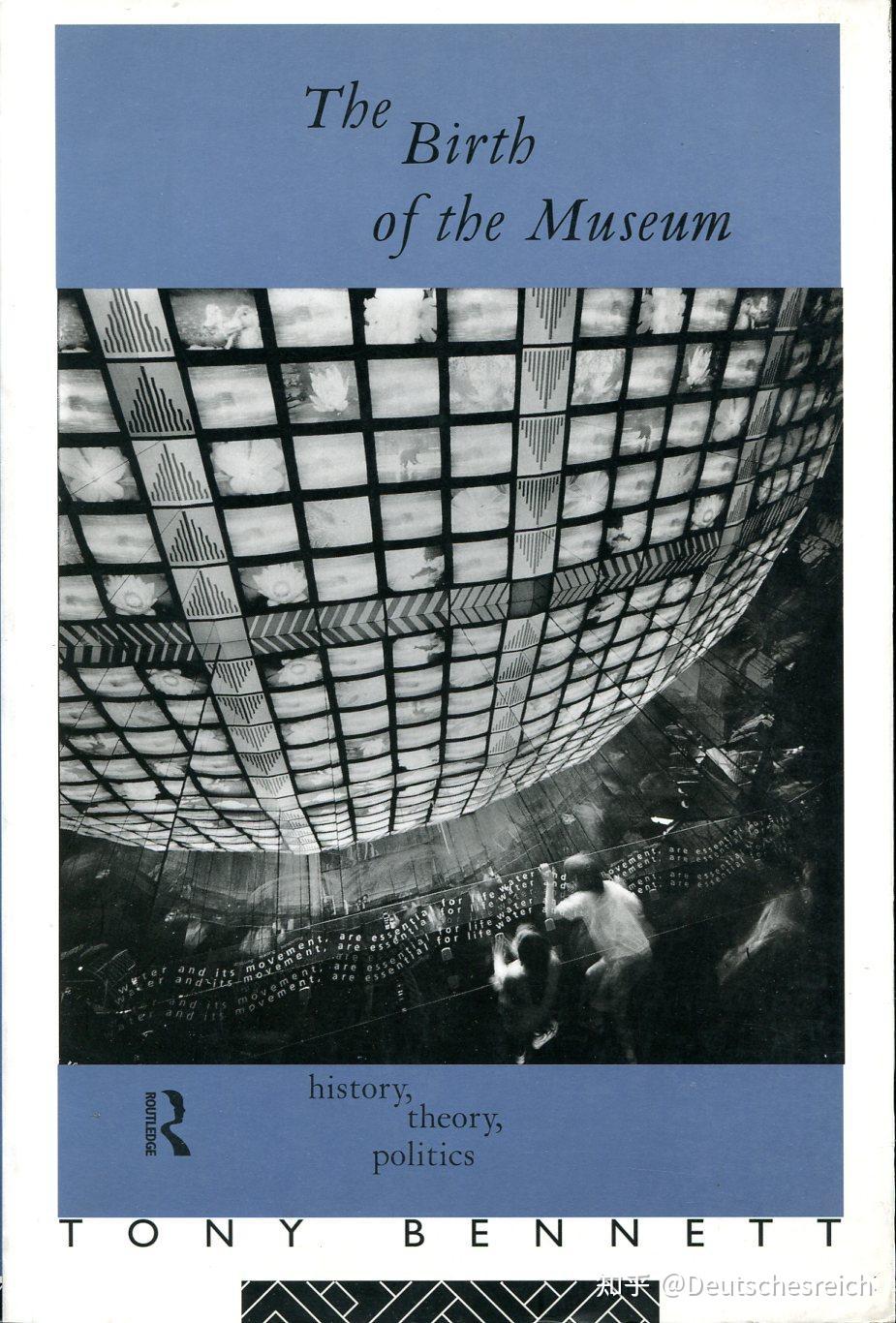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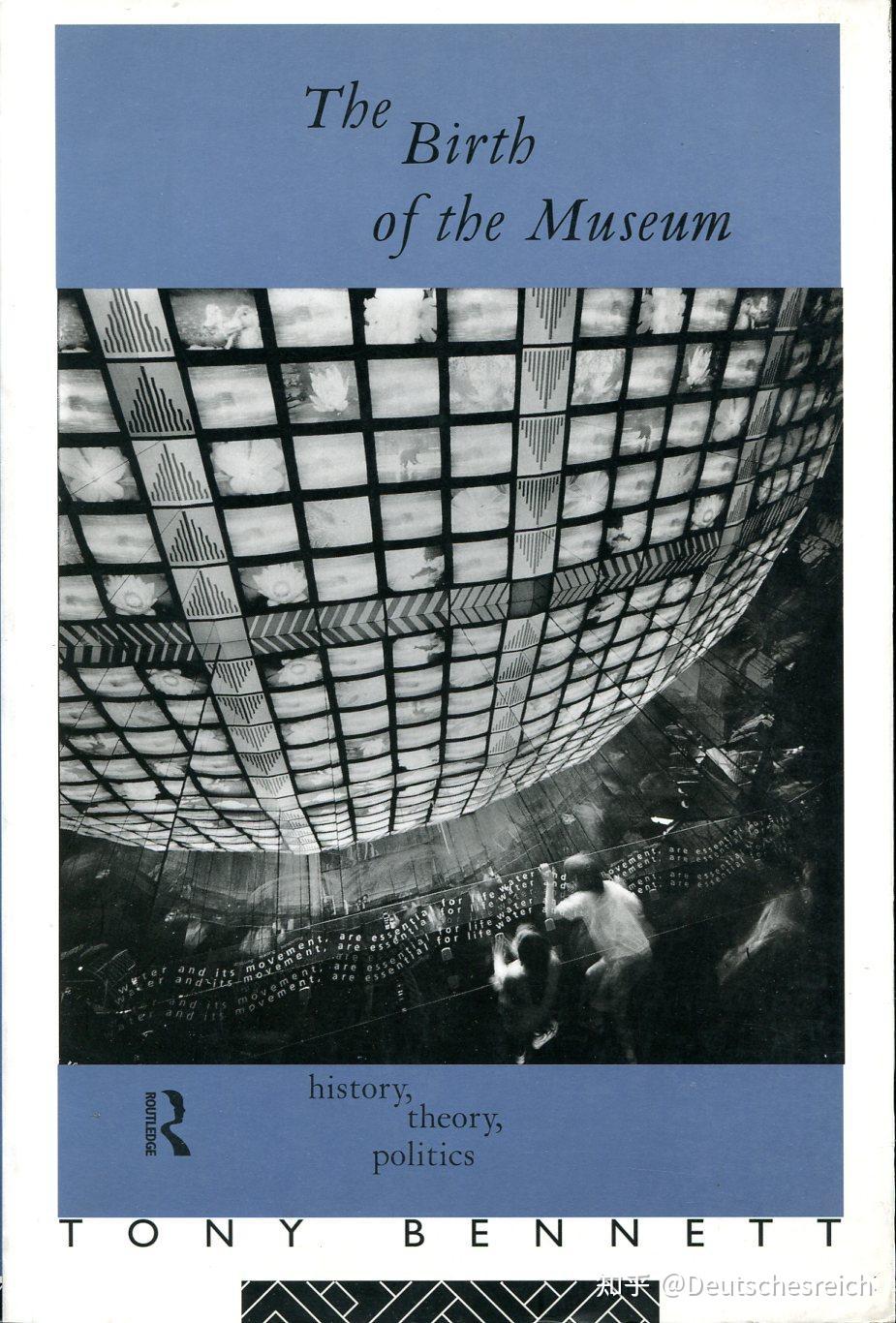
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政治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作者: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 翻译:Deutschesreich
初看书名,读者会以为这是一部讲述博物馆发展史的专著,其实不然,Tony Bennett的《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政治》是一部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著作,这个老头冷静而理性,深受福柯的影响,又特别爱用佶屈聱牙的长难句,阅读起来很费劲。鉴于这本书还没有中文版,我先将序言部分翻译出来。我曾就一些表述的翻译问题联系Bennett,但对方拒绝提供帮助,因此译文如有错误敬请指正,欢迎讨论。
Tony Bennett现在澳大利亚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的文化与社会研究所任职。https://www.westernsydney.edu.au/ics/people/researchers/tony_bennett
序言
米歇尔·福柯在他的文章《论异度空间》中将“异托邦”(heterotopias)定义为“所有可以透过文化找到的现实地点,这些地方是可以同时被展示、被争论、被转化的。”因此,他认为博物馆和图书馆——都是“无限期积累时间的异托邦”——是特有的19世纪西方文化:“积累一切以建立某种综合档案的想法,在一个场所里包含所有时间、所有年代、所有形式、所有体验的愿望,为所有时间建造一个场所,这个场所自身在时间之外,是时间所无法侵蚀的,在一个固定不变的场所,如此组成对于时间的一种永恒的、无限期积累的方案,这全部的想法就是我们的现代性。”
福柯认为,与博物馆、图书馆相反是那些远非累积时间的异托邦,它们与时间的联系“非常短暂,稍纵即逝,不稳定,以节庆的方式计时”。依照福柯为这种空间提供的范例,他选定了“露天集市,这种位于城市边缘令人赞叹的空地,每年举办一次或两次,集市上满是货架、展品、稀奇古怪的东西,还有摔跤的、蛇女、算命先生,诸如此类”。
这种反面的例子我们并不陌生。事实上,它们构成了话语坐标的一部分,通过这个坐标,博物馆在其19世纪的形式中被认为是通过双重区分的过程而存在。为现代公共博物馆塑造新的展示空间的过程,同时也是构建和捍卫这个展示空间的过程,要确保它是理性和科学的空间,完全有能力承担架在它身上的教育负担。而要顺利完成这样的过程,就要把它与归咎于竞争性展览机构的无序状态区分开来。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我们用来区分博物馆和它们的前身之所在。因此,在19世纪末,这对于博物馆的早期历史学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博物馆狂想家——将其取得的秩序和理性与杂乱无章的不协调性进行对比,后者似乎是好奇心橱柜的特征,而从其自身来看,博物馆已经取代并超越了后者。托马斯·格林伍德(Thomas Greenwood)在1888年就告诫那些会参观英国小城镇博物馆的观众,他们应该做好找出“脏乱盛行”的准备。他写道:
“当博物馆的学生看到鲨鱼牙制成的项链环绕着一只中国女人的靴子时,或者克伦威尔的士兵头盔里装着古罗马的东西时,他们守序的心灵会被吓到。另一个角落可能有一具装在中世纪的箱子里的埃及木乃伊,好奇的游客可能还会惊奇地发现,在藏品中有本郡的一个优秀板球运动员的奖杯,甚至是一只毛绒玩具狗的残件。”(Greedwood 1888: 4)相比之下,在根据《博物馆或公共图书馆法案》建立的新博物馆,格林伍德断言,由于负责管理这些博物馆的机构的民主成分对“因循守旧或愚蠢的程序”的限制,“秩序和系统正在从混乱中走出来”。
要说理性化的效果是受公民的民主影响确实有些罕见,尤其是在英国。[1]因为更多的时候是科学使博物馆的展品受到理性影响的责任。的确,就想通常说的那样,博物馆从无序到有序的发展史就是博物馆从谬误到事实的科学进程。因此,戴维·莫里(David Murray)认为现代博物馆显著的特征是“专业化和类别化”,即一系列专业博物馆(地质、自然、历史、艺术等)的形成,每件展品都是精心布置的,以便能够理解科学的世界观。莫里称,与这种教育目的相对的是,旧式博物馆更注重猎奇。这就要把重心放在稀缺的和独一无二的物品上,关注点在单个物品的个性而不是共性,鼓励注重轰动效果而非理性和教育意义的展示原则。在莫里看来,在早期的解剖学收藏中发现的道德化的骨架因此取得了如此轰动的效果,只是以不协调为代价,使其教育潜力化为乌有。
“例如,德累斯顿的解剖标本布置得像个游乐园。骨架与树枝相互交缠形成树篱,构成了景观。解剖的主题难以领会,一旦看明白了,大多数是由以下构成的:在莱顿,他们有一个驴的骨架,上面坐着杀死自己女儿的女人;有一具坐在牛身上的男性骨架,此人因偷牛被处死;还有一个被绞死的年轻小偷,他是新郎,新娘站在绞刑架下……(Murray 1904: 208)类似的不协调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在天然或人工制造的商业展览中,在巡回动物园或马戏表演中,尤其是在集市中,他们形成了周围文化环境的一部分,博物馆不断试图从中解脱出来。因为福柯所说的集市并不仅仅是以一种与博物馆不同的方式与时间发生关系。它也不仅仅是以不同的方式占据空间,暂时居住在城市的郊区,而不是长期居住在城市的中心。集市直面并羞辱博物馆,将其作为“非理性”和“混乱”无序的体现,这也是博物馆前身的特点。可以说,博物馆自己的前史在困扰着它。
维多利亚国家博物馆在成立之初(19世纪50年代)就强调要展示“小而丑的生物”以及“绚丽的”的生物——也就是说,是展示的教育意义而不是好奇心或观赏性——因此,它所表现出的焦虑与将其与当代流行展览区分开来的需要有关,也与展示其对奇珍异宝柜的历史超越有关。就在维多利亚国家博物馆开放的同一时间,墨尔本也获得第一个永久性动物园,这是一个建在商业游乐园里的室内场所,动物园尽可能多地保留了这个游乐园美好、吸引人的本质。鉴于动物园注重动物的异域风情,游乐园内的各处娱乐设施就侧重天马行空的幻想:“每个晚上都把头伸进狮子嘴的胡安·费尔南德斯(Juan Fernandez)、肥仔、长胡子的女人、埃塞俄比亚人、巫师,以及台球、靶场、木偶和保龄球沙龙”(Goodman 1990: 28)。如果像古德曼所说的那样,维多利亚国家博物馆向公众展示自己是一个“分类馆”,强调其科学性和指导性,这既是宣布它不是某种马戏团或集市,也是强调它与早期奇珍异宝收藏的区别。
尽管博物馆和集市被认为职能相异,福柯认为在这两者之间的反例过于明显,并且史实薄弱。当然,福柯对19世纪早期叙述的历史新奇性保持充分警惕,这种叙述将博物馆和集市的出现视为对立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去留意历史进程,这种进程随后削弱了那个反例的概念。在19世纪晚期出现了另一种“异度空间”——固定地点的游乐园,这种游乐园处于福柯对博物馆和旅游博览会的对立价值观之间的某个点,这个程度具有重大意义。
这里形成的演化是美国式的。从19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Coney Island的一系列游乐园成为这种“异托邦”的范例。在保留了一些流动集市的元素的同时,游乐园将这些元素和从公共博物馆项目中衍生出来的元素进行了混合和合并。在游乐园的嘉年华在提供放松或正常行为的反转时,保留了“节庆模式的时间”的承诺。可是,尽管初期对传统集市的穿插表演(即福柯所说的摔跤手、蛇女和算命先生)持宽容态度,这种宽容往往是经过挑选的,而且随着形式的演化变得更加严格,因为游乐园渴望以公共公园运动为榜样,尽量使自己远离任何可能有损健康的家庭娱乐气氛的事情。
此外,这些穿插表演越来越多地与游乐园的现代性精神和它的承诺相冲突,就像博物馆一样,它致力于积累时间,致力于不可阻挡的进步势头,而游乐园以其特有的形式“欢呼”(强调“新”和“最新”)和娱乐(机械游乐设施),声称既代表又利用大众愉悦的事业。当然,它们在进步的演化时代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它们为游客提供机会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它们将这个时代纳入规范其行程的表演制度中。然而到了19世纪末,博物馆和游乐园都参与了阐述和传播相关的(尽管很少是相同的)时间概念。这对旅行集市来说并非没有影响,它将新的机械游乐设施与摔跤手、蛇女和算命先生放在一起,从而包含了各种时间的冲突,而不是一个单一的、短暂的时间,可以简单地与现代性的累积时间相对立。
与传统的流动集市不同,固定地点的游乐园为现代提供了具体体现,与它们的巡回前辈不同,这种游乐园运行规范、行为得当。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集市以及所有流行场所就是无序管理的标志。与此相反,对游乐园的文化意义的早期社会学评价认为游乐园能够成功地和平管理一大群人,远远比改良或理性消费的公共或慈善事业有效。[2]
到19世纪末,游乐园的出现削弱了博物馆和集市两个异托邦之间严格的二象性,被视为使时间和空间的对立具象化。然而,贯穿19世纪后半段的国际博览会的早期历史已经为这种情形做好了铺垫,在博物馆和集市二者之间提供了互动区域,尽管博览会没有消除二者的不同身份,但还是间接地在持续不断的、多层面的彼此交流中参与进来,削弱了内在的对立性。如果说Coney Island的游乐园的最直接灵感是1893年芝加哥哥伦比亚博览会的休闲区,那么可以肯定芝加哥博览会的休闲区深受博物馆实践的影响。
在这方面,博物馆人类学在协调游乐场的表现视野与进步的意识形态主题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尤为重要,尽管在这一事件中,流行的表演技巧的传统往往使人类学在进化等级中对文明进行排序的科学主张黯然失色。然而,有很多其他方法(暂且不论让它们保持不同的努力)让集会、博物馆和博览会的活动相互作用:今日的主要大都市的博物馆的基本收藏是国际博览会的遗产;博览会掌控密集人口的方法影响了游乐园的设计和布局;19世纪欧洲和北美的自然史博物馆的很多标本是动物收藏中介的网络的功劳,通过P.T. Barnum为他的马戏团、动物园和小博物馆供应活体动物。
在这项研究中,我的组织重点来自博物馆。的确,我的目的——至少是好的那方面——是为现代公共博物馆提供侧重政治的谱系。我说的“谱系”指的是博物馆的形成及其早期发展,这将有助于在博物馆政策与政治的问题中阐释坐标,这些问题已经出现,并将继续存在。因此,这个解释被视为对共同事业做出的贡献。因为现在有许多这样的历史,它们希望解释博物馆的过往,这将证明比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仍然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更有利于当今的博物馆辩论和实践——这些解释是以博物馆早期编年史来叙述的。[3]然而,这里提供的解释与其他类似的努力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对博物馆谱系学可能有用的任务进行了批判性的构想。例如,Eilean Hooper-Greenhill提出的博物馆谱系主要关注博物馆内部的那些分类和展示的实践以及这些实践所隐含的主体地位的相关变化(Hooper-Greenhill 1988)。相比之下,我要论证博物馆的形成也需要与一系列附属文化机构的发展联系起来看,包括明显陌生和不相关的机构。
当然,博览会和展览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对象。如果说博物馆被设想为有别于展览会并与之相对立,那么在设想其与其他民众集会场所(尤其是公共场所)的关系时也是如此。同样,博物馆无疑也受到了它与文化机构关系的影响,这些文化机构与博物馆本身以及早期的国际展览一样,都有一个理性和改善的方向:例如图书馆和公共公园。尽管如此,一些特征使博物馆、国际展览和现代博览会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而与众不同。这些机构中的每一个都参与了“展示和讲述”的实践:也就是说,以一种旨在体现和传达特定文化意义和价值的方式来展示文物和/或人。这些机构在向所有人开放的同时,也表现出同样的担忧,即制定规范参观者行为的方法,而且最好是以不引人注意和自我维持的方式进行规范。最后,由于认识到参观者的经验是通过他们在展览空间中的身体运动来实现的,所有这三个机构都对规范参观者行为的表现性表示关注。克服身心二元对立,将参观者视为“长在腿上的脑子”,每个机构都以其不同的方式,成为“有组织的行走”的场所,在其中以(或多或少)指导性的行程形式传达预期的信息。
尽管如此,尽管这些展览机构的实践有其独特性,但也需要从它们与影响相关文化机构的更广泛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来看待这些变化。在这方面,我对“博物馆的诞生”的描述是这样的:对博物馆、博览会和展览之间关系的关注是为了作为一个更广泛的历史论证的手段,其关注点是19世纪文化领域安排的转变。
这些是构成第一部分的各章中所涉及的问题。这里有三个问题是突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公共博物馆在哪些方面体现了一种新的“政府的”文化关系的发展,在这种关系中,高雅的文化作品被视为可以用新的方式成为社会管理的工具。这就需要考虑博物馆在为文化作品提供新的环境的同时,如何作为一个技术环境重新塑造文化艺术作品,以便让这些作品用于新的目的,成为政府项目的一部分,旨在重塑社会行为的一般规范。
由于被认为是能够“提高”民众文化水平的工具,19世纪的博物馆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如何规范参观者的行为。其他19世纪的机构也面临着类似的困难,这些机构的功能要求它们自由地接纳没有区别的大众:例如铁路、展览和百货公司。这带来的行为管理问题引出了各种建筑和技术解决方案,这些方案虽然起源于特定的机构,但往往又被迁移到其他机构。因此,第一部分的第二条分析线索是,在博物馆、展览馆和百货公司中发展起来的行为管理技术,后来是如何被纳入游乐园的,这些游乐园的设计旨在将展览会变成一个监管的领域。
第三组问题集中在与公共博物馆相关的代表空间和它所产生的政治。在《事物的秩序》中,福柯提到了人类科学中“人的经验性-超验性双重性”所扮演的暧昧角色:人既是这些科学所显示的对象,又是它们所提供的知识的主体。正如福柯所说,“人以其模糊的地位出现,既是知识的客体,又是认识的主体;被奴役的主权者,被观察的旁观者”(福柯1970:312)。我们将论证,博物馆也在它所组织的知识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中建构了人(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性别化的形式在历史上是合适的)。在组织不同类型博物馆(地质学、考古学、人类学等)的展示框架的学科之间的关系中,它的表现空间将人——进化的结果——设定为知识的对象。同时,这种表现方式为参观者构建了一个已经实现的人类的位置,位于进化发展的末端,从这里可以理解人类的发展和它所包含的附属进化系列。然而,在这个表现空间中,在它所构建的知识主体和对象(人)的明显普遍性与这种普遍性在博物馆展示中实现和体现的总是社会性的和特殊的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为当代博物馆政策和政治的出现提供了——并将继续提供——话语上的协调,以确保不同群体和文化在博物馆展览实践中的相等平价(parity of representation)。
如果说这一要求构成了与博物馆有关的现代政治辩论的一个独特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则包括现在或多或少的规范性要求(尽管这一要求在理论上比在实践中更受尊重),即公共博物馆应该向所有阶层的人平等开放。虽然这一要求部分地体现在现代博物馆作为公共博物馆的概念中,但它的地位一直是,而且仍然是有些矛盾的。因为,为了国家或整个社会的利益,我们可以期望博物馆的仁慈和不断改善的影响能够影响到所有的人群。或者说,也可以将其主张为一项不可侵犯的文化权利,所有民主国家的公民都有权主张这一权利。这两种概念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博物馆观众统计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有了粗略的观众统计,但只是以允许将总观众人数与一周中的几天或一年中的时间联系起来的形式。这些数字最早的政治用途是证明晚上、银行假日和——当周日允许开放时——周日的参观人数增加。像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和后来的托马斯·格林伍德这样的改革者将这些数字作为证据,证明博物馆有能力将文化的改善力量带给工人阶级。这种对衡量博物馆文明影响的关注既与以文化权利为由改善博物馆使用权的关注有关,但也有区别--这个问题直到后来对博物馆参观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的研究表明了社会上不同的使用模式时才出现的。更重要的是,如果相邻领域的发展能够说明问题的话,强大的意识形态因素阻碍了这类信息的获取。爱德华·爱德华兹(Edward Edwards)是英国公共图书馆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严厉指责地方公共图书馆获取用户的职业信息是未经授权的,与他们的目的无关。[4]
关于博物馆游客研究的历史还有待更充分的研究。然而,似乎很清楚的是,明确提出的让所有阶层的人都能参观博物馆的要求,与统计调查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些调查使参观公众的社会构成清晰可见。这些研究最早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属于战后时期。[5]尽管如此,文化权利原则现在在公共博物馆中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虽然实施这些原则需要依靠外部监测设备,他们显然也受到了博物馆形式的内部动力的推动,在其建立的公共空间中,权利应该是普遍和无差别的。
那么,这些就是本研究第一部分所回顾的主要问题。虽然这里归纳的三个章节中的每一章都有关于这些问题的内容,但它们的重点和侧重点以及理论方法的角度都不同。在第一章“博物馆的形成”中,主要的理论坐标由福柯的自由政府概念提供。在第二章“展览综合体”中,重点在于福柯对应用于博物馆的学科权力的理解,以及如何通过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权力的修辞策略进行有益的调节,从而使其产生的洞察力。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章,“博物馆的政治合理性”,主要是再次关注福柯,尽管是他作品的另一个方面。在这里,福柯关于监狱的著作被视为一种模式,用来说明当代博物馆政策和政治的许多方面是由支配博物馆形成的话语坐标所产生的。
我认为,在现代博物馆方面产生了两种独特的政治要求:要求在博物馆的收藏、展览和保护活动中,所有群体和文化都应该有平等的代表性;要求所有社会群体的成员都应该有平等的实际和理论权利进入博物馆。关于这些政治要求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更详细和具体的例子构成了本研究的第二部分的主题。如果说,在第一部分中,我关注的是追踪那些允许现代博物馆政策和政治出现并形成它们的条件,那么第二部分的重点则转向从我所称的博物馆“政治理性”的角度对特定的当代政治和政策问题的具体参与。
然而,本书这一部分的重点有所扩大,我的注意力不再仅仅局限于公共博物馆。在第四章“博物馆和‘人民’”中,我考虑了“人民”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博物馆的展示实践中可能被代表的竞争和矛盾的方式。为了展示一些有效的对比,我在这里讨论的范围包括通常与露天博物馆形式相关的浪漫的民粹主义,以及支配许多当代澳大利亚博物馆装置的社会民主的“人民”概念。我还评估了更激进的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概念,通过考虑格拉斯哥无以伦比的人民宫的例子,对“人民”的形式进行了最适当的表述。
下一章“哪些过去?”扩大了讨论的范围。它考虑了对适合社区不同群体的兴趣和价值观的代表过去的形式的要求可以扩展到公共博物馆以外的方面。这种要求可以包括遗产地,就像它可以适用于从特定社会的整个博物馆和遗产地中产生的过去的画面。然而,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中,重点回到了公共博物馆,尤其是公共艺术馆。借鉴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论点,“艺术与理论:无形的政治”探讨了艺术馆的展示实践与社会使用模式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在所有的公共收藏机构中,艺术馆仍然是最不容易被公众接触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继续致力于展示的原则,这就意味着展示的艺术的秩序对于那些还没有配备适当文化技能的人来说是不可见的,也是无法理解的。这种根深蒂固的立场现在看来越来越任性,因为获取和公平的概念已经渗透到文化的所有领域,并使这些领域的公共开支合法化。
在本书的最后部分,我的注意力回到了博物馆、博览会和展览,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然而,现在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些问题。在这里,我考虑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形成过程中,博物馆、博览会和展览作为进步技术的不同方式。这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事实上,在当时,博物馆等被称为 "进步的机器 "是很常见的。我想说的是,这样的比喻绝不是错的。作为一种文化技术,博物馆、博览会和展览通过对其所构成的表征、常规和规则的衔接组合来实现其有效性,它们的概念和功能确实具有类似机器的一面。然而,这一论点的阐述涉及到一个视角的转变。它要求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些机构是如何表现进步的——因为这是相当熟悉的领域——而且还要考虑这些表现被组织成表演资源的不同方式,这些表演资源对参观者的行为以及他们的认知视野进行编程。这将涉及到将这些进步的表述视为游客可能利用的道具,以实现特定形式的自我发展——自我的进化练习——而不是仅仅作为文本制度的一部分,其影响具有修辞或意识形态的性质。
第七章“博物馆与进步:叙事、意识形态、表演”在回顾19世纪末自然历史、民族学和解剖学藏品的布局的各种不同方式中展开论证,以便让参观者重走从简单到更复杂的生命形式的进化发展道路。这一论点通过考虑皮特·里弗斯展示 "野蛮人"及其手工艺品的类型系统是如何构成一个“进步的机器”,在寻求促进进步的同时也试图限制和引导它。接下来,我们将考虑19世纪博物馆的进化叙事和路线在其结构中以及在其产生的表演性可能性中是如何被性别化的。
下一章,"未来事物的塑造:88世博会",考虑了国际展览的形式如何发展到提供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参观者被邀请对时代进行不断的更新或现代化改造。在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布里斯班的 "88世博会 "时,本章还考虑了进步的修辞与国家和城市的修辞相结合的方式,以提供一个复杂的组织环境,向许多不同类型的社会表现开放——事实上,是为其设计的。最后,在第九章,"一千个一万个麻烦。在第九章 "黑池欢乐海滩 "中,我的注意力转向了进步的修辞学如何渗透到整个城市的环境中,但我特别关注黑池的集市——欢乐海滩——在那里,进步被编码成欢乐的表演,集市上的人被期望进行这种表演。然而,这个关于现代游乐园的详细案例研究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形象地说明与当代博览会相关的现代化和精简的快乐在哪些方面借鉴了博物馆和展览的现代化修辞和技术。
这最后一章还引入了一个限定条件,在开始时提到这个限定条件可能是有用的。我在本书中关注的主要是博物馆、博览会和展览,因为它们的倡导者、设计者、导演和管理者的计划和预测都是这样设想的。这些计划和预测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组织和构建了参观者的体验,或者相反,这些计划的效果在多大程度上被回避、回避或者根本没有被注意到,这些都是不同的问题,尽管它们很重要,但我没有在这里讨论。
我已经提到了我在准备这项研究中所借鉴的一些理论来源。福柯的工作,以其不同的形式和解释,对我来说很重要,就像葛兰西的工作一样,尽管我已经意识到--并且没有试图掩饰--这两者之间经常存在的尴尬和不安的张力。也许值得补充的是,随着它的发展,我在这一领域的工作更倾向于福柯而不是葛兰西的范式。
皮埃尔·布迪厄的工作也很有价值,因为它揭示了博物馆,特别是艺术画廊的矛盾动态。虽然画廊在理论上是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机构,但它通常被统治的精英们占有,作为那些 "区别"表演的关键象征场所,通过这些表演,知识分子(cognoscenti)将自己与 "大众"区分开来。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关于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历史论点也很有帮助,尽管我一直小心翼翼地将这些论点从哈贝马斯的辩证期望中解脱出来,即这样的公共领域预示着一种更理想的言说状况,而历史还没有把我们送进去。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琼·兰德斯(Joan Landes)、卡罗尔·佩特曼(Carole Pateman)和玛丽·瑞安(Mary Ryan)对公共领域的概念,以及更普遍的公私分界进行了重要的女权主义重新思考。另外,克日什托夫·波米安(Krzysztof Pomian)的工作也很有帮助,他提出了如何将收藏品从它们在可见和不可见领域之间建立的不同类型的契约中有效地区分出来。
我对这套相当多样化的理论资源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实用为导向的。虽然我没有试图否认或压制与我的关注相关的重要理论差异,但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我在本书中的目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只是有选择地借鉴了这些理论传统的不同方面,因为这对于正在讨论的具体问题来说是最合适的。
尽管这是一本由一系列特殊的知识兴趣所驱动的学术书籍,但如果我不是对其主题有相当强烈的个人兴趣,我怀疑我是否应该完成它。虽然传记因素通常最好不说,但在这种情况下,简要地谈一下个人兴趣和投资,这有助于维持我对本书所探讨的问题的兴趣,可能有一定意义。在《圣树林》(The Sacred Grove)中,狄龙·里普利(Dillon Ripley)告诉读者,他的博物馆哲学是在他10岁时在巴黎度过一个冬天时确立的。
小时候在杜伊勒里花园玩耍的一个好处是,在任何一个时刻,人们都可以乘坐旋转木马,满怀希望地去抓戒指。下一秒,人们可能会在栗子和梧桐树之间的小路上徘徊,寻找卖高夫饼的老妇人,那些奇妙的热的威化饼状的东西,上面撒满了糖粉。在时间的第三个瞬间,就有了庞奇和朱迪的表演,这是生活的镜子,现在是滑稽,现在是悲伤。再过一会儿,人们就可以进入卢浮宫的一个画廊了……然后又去了花园,那里的一个角落里有一片沙子,可以堆沙堡。然后再回到卢浮宫,在大画廊里闲逛。
(Ripley 1978: 140)
里普利从这一经历中得出的哲学是,在博物馆的学习环境和有趣的游戏世界之间没有,也应该没有本质的区别;人们应该能够在这两者之间自然地移动。对于一个资产阶级的男孩来说,在博物馆和绅士化的游乐场乐趣之间的这种毫不费力的过渡,无疑是可能的。我自己的经历——我想这是比较典型的——是不同的。对我来说,游乐场比博物馆早,而且早了好多年。集市有各种形式:在醒酒周假期期间在兰开夏郡的城镇安营扎寨的巡回集市;曼彻斯特的永久性游乐园Belle Vue,我父亲在那里教会了我乘坐震耳欲聋的Bobs的白刃术;以及黑池的欢乐海滩,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曾多次参观,后来又把它作为研究对象。当我在成年早期开始探索博物馆和艺术馆的世界时,并没有像里普利所描述的那样有一种毫不费力的过渡感;相反,它是文化行程的一部分,带着一些不情愿的心情去旅行,这需要熟悉一种新的习惯,以便在这些机构中感到宾至如归。然而,同样地,由于我已经提到的原因,去博览会和参观博物馆或展览总是让我觉得是某种程度上的相关活动。
因此,写这本书是为了解释我在参观博览会或博物馆时仍有的"不同但相似"的体验。然而,它的雄心在于从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而不是个人的特质来解释这些相似和不同。
参考
[翻译丨博物馆的诞生:历史、理论、政治(1)] 相关文章推荐:
- 最新经典文章
- 热门经典文章
- 热门文章标签
全站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