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诗人骆一禾?
时间: 2022-07-05 12:30:31 | 作者:王汝滨 | 来源: 喜蛋文章网 | 编辑: admin | 阅读: 100次
- 2023-11-27 12:00:54你能想到的第一句以“贺”字开头的诗词有哪些
- 2023-11-27 03:00:49诗歌中的内蒙古是什么样子
- 2023-11-26 19:01:29屈原可以算爱国诗人吗
- 2023-11-25 23:00:32你能想到的第一句以“仙”字开头的诗词有哪些
- 2023-11-25 16:59:49能不能把浙江省的11个地级市编写成诗词或散文
- 2023-11-25 14:01:30你能想到的第一句以“鄱”字开头的诗词有哪些
- 2023-11-25 14:00:10八言诗与其他体裁的诗歌有何区别
- 2023-11-25 03:00:42如何读诗 感觉进入不了诗歌的世界 听别人评析或看他们的作品总是不明觉厉啊!
- 2023-11-24 16:01:29能不能用诗词题目写一篇诗词、或者散文呢
- 2023-11-23 11:59:59唐朝诗人为什么多而且高产

原标题《骆一禾:在朝霞里我看见我从一个诗人变成一个人》
正文——
最少听见声音的人被声音感动
最少听见声音的人成了声音
头上是巴赫的十二圣咏
是头和数学
沿着黄金风管满身流血
巴赫的十二圣咏
拔下雷霆的塞子,这星座的音乐
给生命倒酒
放干了呼吸,在谁的肋骨里
倾注了基础的声音
在晨曦的景色里
这是谁的灵魂?在谁的
最少听见声音的耳鼓里
敲响的火在倒下来
巴赫的十二圣咏遇见了金子
谁的手斧第一安睡
空荡荡的房中只有远处的十二只耳朵
在火之后万里雷鸣
我对巴赫的十二圣咏说
从此再不过昌平
巴赫的十二圣咏从王的手上
拿下了十二支雷管
——骆一禾《巴赫的十二圣咏》
1989年5月11日,骆一禾写下了他生命里的最后一首诗——《巴赫的十二圣咏》,这首诗是写音乐的,也是写海子的。骆一禾的挚友海子一个多月以前在山海关卧轨自杀,骆一禾也在写完这首诗的三天以后,突发脑溢血晕倒,直至5月31日,离开了这个世界。
海子去世后的一个多月里,处于痛失挚友的震悚中的骆一禾马不停蹄地为海子奔走呼吁——整理海子遗稿、跟杂志社商定纪念专页、联系出版社、写海子评论……终于,切入生命的悲痛与苦熬心神的劳累击垮了他。可以说,骆一禾是用尽了自己最后的生命时光,来试图打开这个世界对诗人海子倾听的耳朵。
而骆一禾无疑是最初对海子完全敞开耳朵的听众。
《巴赫的十二圣咏》首先写的是诗人自己对音乐的感受,其次是描述挚友海子听到巴赫的音乐的激动,而隐藏的一层意思则是:这种听到音乐时的涌动的激情可以类比为诗人阅读海子的感受。海子的住处没有属于娱乐的位置,连台收音机也没有,且海子不喜欢交往,缺少对外物的关注,因此诗里说“最少听见声音的人被声音感动”,指的就是很少听音乐的海子听到了巴赫,而“最少听见声音的人成了声音”则大抵是对“海子成为一种声音被人倾听”的指认。海子去世以后,骆一禾一直埋头在海子的作品中,整理遗稿,撰写评论,除了一直以来对海子创作的谙熟,想必这段时间全身心投入对海子的“倾听”,让骆一禾有了更多深切、直抵内心的撼动。诗里面“沿着黄金风管满身流血”“拔下雷霆的塞子”“在火之后万里雷鸣”这样的描述,除开起自音乐的震撼,更多地混杂了痛失挚友、痛失一个“声音”那种有如万钧的重量和痛感。活的声音已经消逝,如今只剩下纷繁的遗稿,因此最后一段“从此再不过昌平”(海子的住处在昌平,骆一禾时常去昌平访他),令人有悚然一紧的动容。
海子去世后,骆一禾一共写了五首诗、三篇评论,几乎全都与海子有关。这位圣洁的歌者把海子像旷世珍宝一样高高举起,向人展示,细致地展览它的珍贵和特殊,而他似乎完全没有想过在众多歌唱者之中,他自己的声音也是那么高亢、嘹亮、澡雪、绵密、纯血,让人震撼,如闻雷霆……在这一年以后的许多个春天里,一直有人在不断地反复吟咏着海子的乐章,让海子这个名字从一种记忆变成了一种象征,在无数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和春天一起开放,正如海子诗里面写的“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而同样倒在那个春天的,创作了体量不低于海子的具有恢弘气象的诗章的“圣者”骆一禾,则和他沉静温和的性格一样,一直平静无声,渐少被提及,似乎被淡忘。
兴许热闹本来就是虚妄的,真正的知音人常常沉浸在被安静地灼照的时刻,相信这个世上必不会缺少对圣洁的歌者倾听的耳朵。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提及骆一禾必然会提到海子,更多是把骆一禾作为海子的某种注脚,在强调骆一禾之于海子的知音意义的同时,很容易忽略骆一禾本身的生命质感和诗歌分量。不可否认,骆一禾与海子在创作上有一种血亲式的关系,这一方面是二者在创作倾向上的某种暗合与创作实践中的互相映照,隐藏其中的还有某种“解读者效应”,亦即骆一禾这位读者在不断阅读与反馈中对海子的创作产生了某种影响,骆一禾甚至是促成“海子生涯”的一条线索;而海子对骆一禾应该有同等的映照意义,骆一禾在对海子的阅读和创作促进过程中不断地丰满了自己的创作图景。两人在进入的文化空间、对意象和元素的领悟上都有了很多暗合。在创作上,他们是真正彼此促进,互为肱股的血亲兄弟。
海子和骆一禾都是钟情于创作“大诗”的人,曾企图以多人合力,共同创作一首高密度的具有交响乐团式多声部合奏的史诗,骆一禾曾有个宏大的构思,建议他和海子、西川三人共同创作一部伪经,包括天堂、炼狱和地域,其命名就可看出其创作指向具有“经书”的性质。海子的大诗创作《太阳·七部书》的构思延续着这一意图,海子曾幻想一种“众兄弟围坐篝火,共同创作、讨论、说书、讲经、表演”那样一种部落聚会式的共同创作的图景,但是海子在长诗的创作中发现,当时并没有集众人之合力创作大诗的土壤,最后只能孤身挺进,最后败于中途,遁入太阳。骆一禾和海子也都是“熟读经书”的人,海子熟悉《圣经》《古兰经》等经书,也熟读《罗摩衍那》、荷马史诗、《神曲》《浮士德》等不同文化部落的史诗,而骆一禾甚至能背诵《新约》和《旧约》里的原文。这些相似和统一的创作倾向,高度重合的阅读背景和文化库,让他们彼此欣赏,彼此影响,共同在诗歌中挺近,成为了诗人交往中令人称羡的现象,由于两人共同擦亮的一个诗歌意象“麦地”,被诗评家燎原称为“孪生的麦地之子”。
因此,骆一禾对海子不仅有敞开耳朵的知音意义,他更像是一个提着油灯和辟路刀的引路人,率先明确方向,带队前行。海子死后,骆一禾曾在日记里写道:“上帝,你杀死了我自己的一个儿子。”这种表述令人震惊,它所认定的血亲关系不是“兄弟”,而是“父子”,这种夸张地表达悲痛的方式很显然表露了骆一禾的一个实际的心思,那就是他在“海子生涯”中扮演过为父为兄的角色。张玞还提到,海子有一次在骆一禾家里,坐在床头生闷气(大概是受到了诗歌圈的冷遇),骆一禾则背诵着海子的诗,对他说:你的诗,多好!骆一禾在海子的创作中扮演的角色从这个场景中就可见一斑。海子在创作上也得益于骆一禾的精神光照,骆一禾的那种广阔的精神关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他渊博的学识和系统理论的诗歌美学,这些都不断对身边的诗友产生着影响,海子无疑是其中汲取最多,受影响最大的一位。
骆一禾与海子的不同主要体现在气质上,海子身上有那种农村孩子式的野性、颟顸、质朴的高傲,同时自卑、敏感、不善言辞;而骆一禾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有着儒雅、纯正的品质,他待人和善,精力充沛,热衷于交往,是一个常常被同龄人引为兄长的角色。西川说骆一禾“文雅、渊博、深刻、正直、爱朋友”,又说“一禾是我的良师,八年来我受益于他”,可见骆一禾在他朋友心中的影响力。骆一禾的妻子张玞说:“当年一禾就是以他的人格魅力,给很多朋友造成了深刻的印象,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我自己也汲取了一种力量……”骆一禾带给人的是一种表里如一的纯粹与纯净,平易中透着高导的人格气质与不盛气凌人却足以服人的诗品和学养。
从诗歌创作方式看,海子选取的是一种“狂飙突进”式的写作方式,特别是他生命的后期,他是以燃烧生命的方式来试图完成自己的诗歌理想。海子一方面赞赏那些短命的天才们,不节制地挥霍生命意象,蒸腾脑力,倾心死亡,一方面又企图抵达宏伟壮观的史诗,这是非常矛盾的。而骆一禾是反对这种写作方式的,骆一禾认为海子的道路“不但充满了危险,而且潜伏着毁灭性:它必然意味着激情方式与宏大构思之间的根本冲突”,“冲击极限”的这类诗人“都具有显著的才华而归于短命或迷狂”。同样力行着“大诗”的诗歌理想的骆一禾则处于一种更加从容的创作完型中,抛开二人诗歌意图、构型思维以及意象选取上的相近,骆一禾的长诗和他的短诗一样呈现出来一种相对沉潜内敛的气质。相较而言,海子的创作不事克制,他是一个天然占有语言的天赋型诗人,在创作中几乎是挥霍式地铺排意象,不节制语言的自我蒸腾幻化;而骆一禾具有更强的结构意识,其作品呈现出来更加整饬雍容的气象。“如果说,海子是黑暗中一只野蛮的、扑向太阳的血淋淋的豹子,骆一禾则一直身处光明中,优雅、高贵、干净,是王子与圣徒自身的显形。”(燎原《海子评传》)如果不是因为生命的意外,按照既定的节奏书写下去,骆一禾必能呈现远超当下体量的高密度文本,他所创作的《世界的血》与未完成的《大海》也许只是他长诗创作的一个开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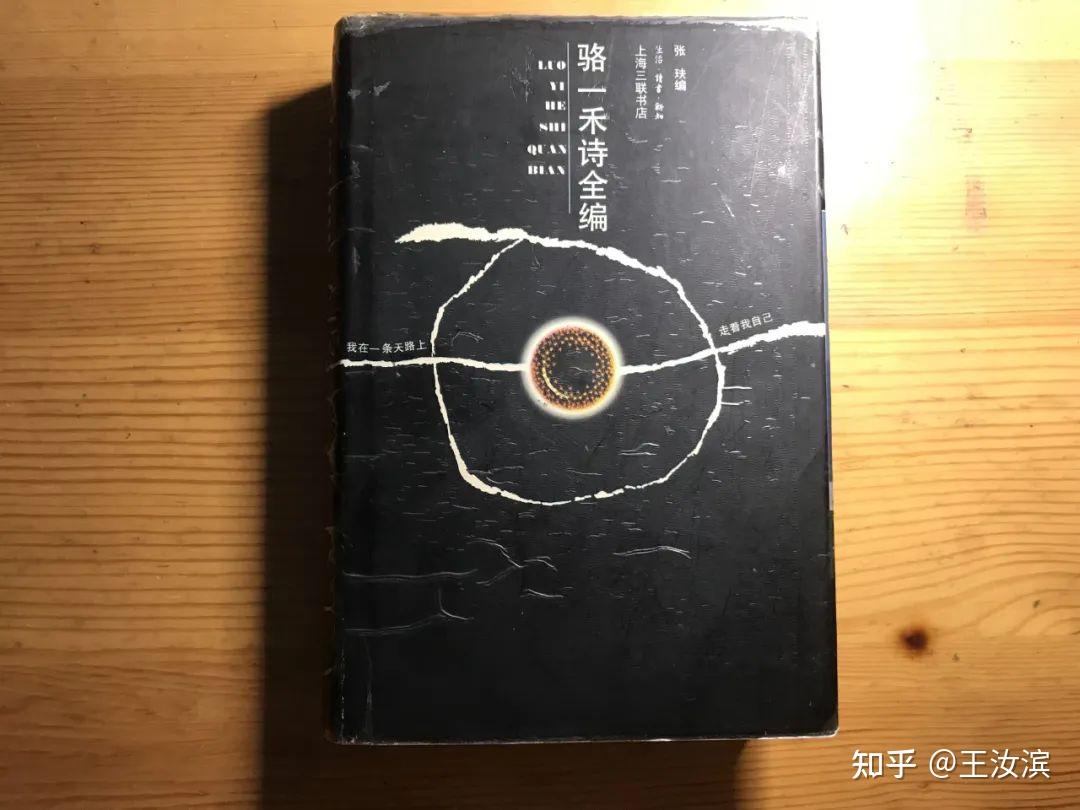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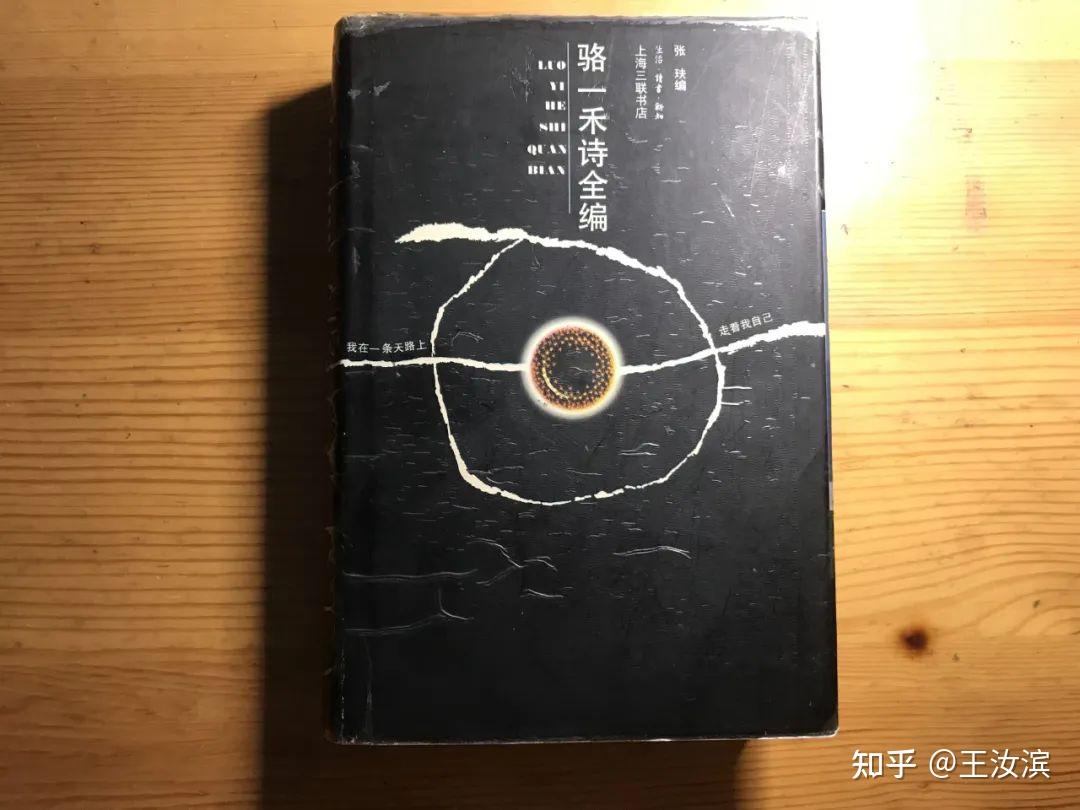
骆一禾最为人激赏的诗作之一是他写于1988年10月的《修远》一诗——
触及肝脏的诗句 诗的
那凝止的血食
是这样的道路 是道路
使血流充沛了万马 倾注在一人内部
这一个人迈上了道路
他是被平地拔出
那天空又怎能听见他喃喃的自语
浩嗨 路呵
这道路正在我的肝脏里安睡
北风里 是我手扶额角
听黑夜正长歌当哭
那黑夜说 北
北啊 北 北和北
想起方向的诞生
血就砍在了地上
我扶着这个人 向谁
向什么 看了好久
女儿的铃铛 儿子的风神 白银的滋润
是我在什么地方把你们于毁灭中埋葬
方向方向 我白银的嗅觉
无处安身 叫我的名字
浩嗨 嗨呀 修远
两代钢叉在水底腾动
那声息自清澈里传来锐利和痛疼
那亚细亚的痛疼 足金的痛疼
修远 这两个圣诉蒙盖在上面
我就看见了大盾的尘土
完人和戈矛 雅思与斧钺
在北斗中畅饮
是否真有什么死去 我触摸着无边
触摸着跪上马头的平原
眼也望不到,脚也走不到
女仙们坐在月亮的边缘
修远 我以此迎接太阳
持着诗 我自己和睡眠 那一阵暴雨
有一条道路在肝脏里震颤
那血做的诗人卧在这里 这路上
长眠不醒
他灵敏其耳
他婴童 他胆死 他岁唱 他劲哀
都已纳入耳中
听惊鸿奔过 是我黑暗的血
血就这样诞生了
在诗中我看见的活血俱是深色
他的美 他的天庭 他的飘风白日
平明和极景
压在天上 大地又怎会是别人的
在诗里我看见活血汪霈而沸腾
沐与舞 红与龙
你们四个与我一起走上风鸣马楚的高峰
修远已如此闪亮
迎着黄昏歌唱
我们就一直走上了清晨
那朝霞
诗人因自己的性格而化作灰烬
我的诗丢在道路上
一队天灵盖上挖出来的火苗
穿过我的头顶
请把诗带走 还我一个人
修远呐
在朝霞里我看见我从一个诗人
变成一个人
与罪恶对饮
说起修远
那毒气在山中使盛水的犀杯轰然炸裂
满山的嵩岳 稀少的密林
那亚洲白练
那儿子的脚跟 女儿的穗佩 口的粮食
身上的布袋与河流亮丽的分叉
连你们也不知道我为什么看着道路
修远呐
与罪恶迎唱 拉开我的步伐
这就是我的涵歌
在歌中我们唱剑 唱行吟的诗人冒险行善
这歌中的美人人懂得
这善却只有等到我抵家园
唱吧 那家乡
我们分别装入两支排箫
素净两方门窗
这声息一旦响起
就不知道黯淡怎样吹过
天就一下子黑了
在大地的口中 排箫哭着
与罪恶我有健康的竞技
说一声修远
三种时间就澎湃而来
天空在升高中醒了
万物愈是渺小 也就愈是苍莽
在那一夜滂沱的雨水中
新月独自干旱
——骆一禾《修远》
西川认为“修远”一词正可作为骆一禾诗歌创作的一个宗旨,也是他做人的一个写照;同样短命的天赋型诗人戈麦对骆一禾无比激赏,他将《修远》一诗抄录在床头,反复吟诵;据说,那时有些年轻人大声诵读《修远》一诗竟至泪流满面;诗人陈东东认为《修远》实在是一首不可(无须)释义而只需反复咏赞,倾听其诗歌音乐的诗。
修远,“路漫漫其修远兮”,修炼生命意志的道路是漫长的,也是高远的,“修远”即立下那种高远的意志,不断求索;“修”另有“修正、修建、整饬、撰写、学习、修美”等丰富的内涵,骆一禾的“修远”是自身盛美之道的修行,是一种个人道德高标的持守。燎原认为,“骆一禾比之海子更为动人的,则在于其精神中葆有的、被这个时代久已忘记了的那种高洁的品性和心地。”西川说,“……恐怕在我将来的岁月里,再也不会遇到一个像他这样近乎完美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在人格高地的人才能契合于“修远”二字,他正是把作诗和做人融为一体,将精神的澡雪、人格的高迈变成诗歌的一部分。他的崇高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真实声音,他不以自恋之姿孤高自赏,而以谦冲沉着的姿态揭示人类智慧和文明,将自己置身于朝霞、血光、飘风白日、平明和极景中,让修远的理想冲涌着自身灵魂,既是自我道德律的宣示,也是对诗的修炼道路的探求。在这里,诗人所意识到的是诗与人格(也即作诗与做人)必然存在或者必须完成的同一性,拒绝生命修炼的诗人只是言语的巨人,其诗作也容易成为无实质意义的聒噪。因此,诗在高超语言技艺的属性之外,更应是一种人生的诫命,精神的指南。“请把诗带走 还我一个人/修远呐/在朝霞里我看见我从一个诗人/变成一个人”,从诗人变成一个人,正是诗人能够直面生存的黑暗,敢与罪恶对饮的生命伟力。在这首诗里,骆一禾精神的纯一性得到了丰沛的昭示,而他的谦抑与内敛,让他不会作道德圣人的舞蹈,而是以排箫奏诵于暗夜,如雨后夜晚,“新月独自干旱”。
《修远》果真是一首值得反复吟诵的诗,沉浸在这三十多年前的高洁声部里,我们也许能升腾起一种纯美的渴望,灵魂为之一澈,在一种光明洁净的图景里安置此刻荒疏的心灵。
三十三年前的今天,骆一禾在病房静躺过十八天以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世界失去了什么,在短暂的纪念完成之后,骆一禾不仅在他自己的创作道路上,也在这个世界上退场了,就像诗歌在大多数人的世界里退场了一样。在整理出版海子遗稿的时候,骆一禾曾说,“在我们这里,无法指望五十年或一百年之后会有人重新发现一个过往的诗人。”骆一禾退场之前,倾尽生命之力把诗人海子推到了世人面前,让他“活了下来”,而等待骆一禾的又会是什么呢?我们相信,这个名字,不会被遗忘,而将在无数个未知的精神奥宇里,熠熠闪耀。我们不指望一个诗歌逐渐退出大众视野的时代,人们会给予诗人多大的关注,也不指望一位业已逝去的诗人还能得到什么样的桂冠,但这位曾与海子做为创作上的肱股兄弟,双峰并峙地占领一座诗歌高地的圣洁歌者,至少应该得到和海子同等体量的关注,他洋洋丰沛的绚烂诗章也应该得到深入的探析。或者,那些诗界的专业工作我们无能过问,今天,让我们至少好好读一首骆一禾吧。
(王汝滨 2022年5月31日于长沙)
王汝滨,原名王利兵,1989年生于河南襄城,诗人、自由撰稿人,著有诗集《我酒杯倒倾》。
[如何评价诗人骆一禾?] 相关文章推荐:
- 最新散文
- 热门散文
- 热门文章标签
全站搜索